“陷阱取证”获取的证据会得到法院支持吗?
时间:2023-01-02 点击: 次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任文岱 - 小 + 大
|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取证难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陷阱取证”往往成为权利人采用的取证方法之一。“陷阱取证”通常指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权利人不暴露真实身份,以普通顾客的身份购买侵权产品或取得其他相关侵权证据,以证明侵权行为存在的过程。而“陷阱取证”获得的证据能否被采用,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近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裁定一起专利权侵权纠纷案件,案中原告不仅试图利用“陷阱取证”方式将案件管辖地改为北京市,还将配合其取证的一方作为被告之一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权并获得相应的损失赔偿。最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裁定对该案不具有管辖权,同时驳回原告对配合其取证一方被告的起诉。 基本案情: 湖南某制药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为一项药品专利的专利权人,其认为广东某制药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一)制造、销售的一款药品(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侵害了其专利权。2020年8月10日,原告委托代理人在公证人员陪同下前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某大药房,以普通消费者身份从该大药房购买了被诉侵权产品10盒,并取得收据一张。 随后,原告以该大药房(以下简称被告二)销售该款被诉侵权产品且住所地在北京为由,认为本案应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将被告一和被告二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被告二立即停止侵权,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万元并支付合理费用。 在提交答辩状期间,被告一对此案提出管辖权异议。被告一表示,被告二与其并无任何业务往来,被告二是在原告方代理人的“引导”下网购的被诉侵权产品并进行销售,请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本案移送至被告一所在地法院进行审理。审理过程中,被告二提交了一份聊天记录,印证了被告一的说法。该聊天记录系被告二与案外人、原告方人员任某沟通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二原本没有被诉侵权产品,是应任某要求而采购了被诉侵权产品,且其采购的全部药品,均一次性地销售给了原告,款项数额与原告所做公证的购买费用一致。经法院询问,原告亦认可此说法。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要厘清本案的管辖权问题,被告二是否为适格被告是关键。 法院表示,原告主张被告二侵害了其专利权——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以被告二的住所地在北京市为由,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但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被告二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系基于原告的取证行为,应案外人任某的要求而采购了被诉侵权产品并将全部被诉侵权产品一次性向原告销售,且在原告向被告二购买被诉侵权产品前,被告二并未销售被诉侵权产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被诉侵权人基于他人行为而实施侵害知识产权行为所形成的证据,可以作为权利人起诉其侵权的证据,但被诉侵权人仅基于权利人的取证行为而实施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除外。依照上述规定,被告二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正是基于原告的取证行为而进行的,所以原告的购买证明不能作为被告二侵权的证据。故而原告起诉被告二侵权,但并未就被告二存在侵权行为提供合法证据,被告二并非本案适格被告。 最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裁定,认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二的起诉,并将本案移送至被告一所在地法院进行审理。该裁定作出后,各方当事人服从法院裁定,均未上诉。 法官说法: 实践中,出于取证难度、成本等方面的考虑,许多知识产权案件的当事人会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方式进行取证。该条款规定,权利人为发现或者证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自行或委托他人以普通购买者的名义向被诉侵权人购买侵权物品所取得的实物、票据等可以作为起诉被诉侵权人侵权的证据。 根据上述规定,权利人取证的目的是发现或证明侵权行为,且未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这在理论上通常被称为“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此种情形下取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帮助权利人起诉。2002年10月12日通过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也确认了该取证行为在著作权案件中的效力。而上述第七条第一款则进一步明确了其在除著作权之外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案件中亦可以适用。 但在此案中,原告的取证方式则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中的“但书”部分的情形。该条款规定,被诉侵权人基于他人行为而实施侵害知识产权行为所形成的证据,可以作为权利人起诉其侵权的证据,但被诉侵权人仅基于权利人的取证行为而实施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除外。该条款“但书”中规定的“被诉侵权人仅基于权利人的取证行为而实施侵害知识产权行为”通常被称为“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此类行为所形成的证据在诉讼中不具备证明效力。 与“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相比,在“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中,被诉侵权人本无侵权意图,被诉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是基于权利人的行为而产生。从社会效益层面考虑,“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行为会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因为该种取证行为让本无侵权意图的被诉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这种诱发侵权的行为增加了社会中违法行为的总量,破坏了市场秩序,对被诉侵权人的权益也会造成损害。 本案中,原告利用案外人使被告二购进了被诉侵权产品,并在诉前进行公证购买。一方面,原告规避了现行法律法规关于管辖的规定,人为制造“管辖连接点”,即通过“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的方式,将管辖地点确定在北京,以实现其自由选择地域或法院进行起诉的目的;另一方面,原告意图从被告二处获得赔偿。原告的行为是典型的“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被告二本身并无侵权意图,但原告行为使被告二陷入民事纠纷之中,被告二不仅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应诉,还有可能负担重大赔偿责任。在该种情形下,若仍要求被诉侵权人承担相应责任,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与社会公序良俗,更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初衷背道而驰。(本社记者 任文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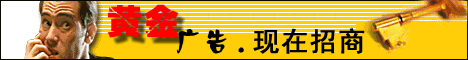
热门文章
最新文章